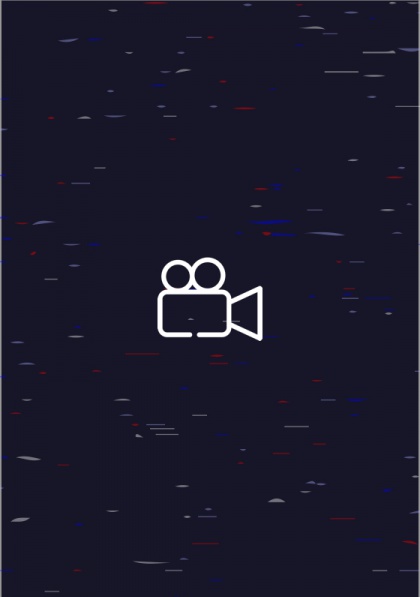
簡介
香蕉王國、電塔之鄉、垃圾鄉、明星災區、飽受土石流威脅的山村......。昔日的繁華,對映著今日的破敗,中寮人心中那個純樸青麗的家鄉早已消失;存在於遙遠遙遠的過去,只能在懷想中相遇......。
然而,九二一地震卻能讓一群人,在中寮相會,展開一段實現夢想的旅程。
本篇圖文著作權為黃淑梅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導演的話
前面有一座山快要崩下來了!不!應該說已經崩落許多土方下來,山又高又陡,下面有許多民房住家,人們不斷地往學校疏散。
我執意要拍山崩的畫面,一開始遠遠地拍,後來找學校的高點拍,但是,角度都不理想,我和攝影師離開學校,走到山對面的一處空地,那裡可以Talley(遠遠地吊拍)拍到正在崩塌的山頭,人們不斷從山腳下流竄逃亡,有媽媽抱著小孩、有老人、有中年人….每個人身上都沾滿了泥巴,人像蟻群般的逃亡,四週的人都在逃難,只有我和攝影師站著不動地拍攝著,土方不斷掉落,掉落的地方裸露出一處處的黃土,原本青翠的山嶺,頓時變成長滿土黃色爛瘡的癩痢山頭。
避難的地方是一處簡陋的木板屋,地下的木板已經腐蛀掉好幾塊,走路要小心,不然,腳一踩空就掉下去了。
許多逃難的民眾橫躺在地上,有個穿暗綠色毛衣的歐巴桑,滿頭亂髮,她的髮絲沾滿了乾掉的泥巴,懷裡抱著的像是她的孫子,歐巴桑不斷地往我這裡靠,似乎在向我求救,她緊緊抓住我的手,張開嘴巴,好像要講話,又像是要吶喊,當她張開嘴時,我發現她的牙齒都不見了,只剩二顆長長、黃黃、黑黑,危危即將掉落的壞牙,搖搖欲墜地立在空空的牙齦的左下方,她黑洞般的雙眼凹陷無神,張著大嘴直逼我而來!我這才猛然覺得她是鬼魅,不是人….
這是我拍攝、剪接《在中寮相遇》這部片子時所做的惡夢。這樣類似的夢境不只一次,而且,夢境總是災難的現場。自拍攝到後期剪接這六年來,從我的身體、意識到潛意識,拍攝現場的種種,總是不斷地在現實生活與夢境中交錯。
我必須承認,拍攝這部921重建的紀錄片,確實耗掉我許多的體力和心力,因為現場的巨大和複雜超乎我原來的想像,但是,我也同時獲得了一個更深層感知台灣這片土地氣息和脈搏的寶貴機會,雖然,在全景工作多年,我一直有很多機會接觸社會各個角落的生活現場,但是,卻從來沒有一次像拍攝921地震這部片子這般深深撼動我內在深處的靈魂。
我是在台南縣白河鎮出生的,從小,就聽聞父母親及一些長輩述說四十幾年前白河、東山大地震時的慘況,母親說,當時她19歲,才聽到「呼!呼!呼」地動的呼號,地牛就以一股強大的力量把土地抬起來「摔」,頓時山崩地裂,房子如骨排般的震垮,人站都站不住,到處黑天暗地,我的阿祖堅持不離開家,窩躲在大神桌底下,不斷地祈禱默念著:『嗷!嗷!嗷!(牛叫聲)地牛乖乖,地牛惦惦,地牛乖,不倘震動!地牛乖!不倘震動!』那時候,許多土角厝倒塌,大家不敢進屋內睡,都拿著草蓆,就地舖上乾稻草,天冷也只能蓋著粗麻布袋將就在外面空地過夜,白河市場因為建築物老舊,許多人被壓死;當時物資缺乏,沒有救濟品,沒有愛心團體,也沒有補助,一切都靠災民自力救濟…
母親說的那些話語結合我的想像,化成一幕幕的影像嵌印在我小小的腦袋中,盡管我不曾親身經歷大地震,然而,『地震』這個印象,人們對『地牛』的敬畏,卻在父母親及長輩們的言語傳述中,成為我成長中一個重要的記憶。
1999年,30歲的我,在921大地震之後,拿著攝影機站在中寮鄉永平街二排倒塌房屋的路上,四週斷垣殘壁,黃土飛揚,災民們個個面無表情,安靜地在倒塌廢墟中收拾殘物,搭理帳棚,突然間,我有一種時光交錯的感覺,眼前這一幕幕的街景,瞬時變成一張張停格的泛白照片…母親年少時的地震記憶,像一條跨越時空的漫長微絲將現在的我和過去的她連結起來,我的媽媽在四十幾年前也曾經歷過這樣一場慘絕人寰的災難,當時,也有很多人跟現在我眼前所見到的這些災民一樣痛失至親吧?那時候的母親,她(他)們是如何度過那場災難的?….當下,我在心中篤定地告訴自己,我要把這一切記錄下來!於是,就這樣展開了我與中寮長達六年的緣份。
地震後第十天,我來到中寮鄉,在中寮人的眼裡,中寮這個故鄉,是一個幾乎從台灣地圖上消失的村落,這個鄉村曾經因為香蕉外銷日本而繁華,卻也因為二次大戰後日本不收香蕉以及城市化,工業化而日漸沒落,中寮的命運就跟台灣許多邊陲的農村一樣,年輕人外流,農業蕭條,再加上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只著力於選舉樁腳的經營,鄉里建設無物,幾乎讓人看不到這個鄉村的未來。
而進入到現場,攝影機開啟越久,身心浸淫在這裡越深,就會發現,地震震垮的不只是表面建築物的瓦解崩塌,隨著這場地震而來的,或說潛藏在這場地震下面的,是更深更廣的人為災難---地方政府長期弱化、污腐以及面對災難的無能;官僚行政體系的末梢神經麻痺;台灣山林土地過度使用、開發而帶來的土石流災難威脅;我只能說,地震震出了台灣長年來底層的文化沉疴。
越貼近現場,就讓人對災難的感受越深刻,也越無力!這幾年,我的攝影機不是在混亂,一再重覆,始終沒有進展的重建會議現場,就是在急切地跟著山上農民逃離土石流的路途中…,我面對的是一個複雜龐大的結構問題,經常在筋疲力盡的拍攝之後,我感覺到一股巨大的無力感,幾乎要將我吞噬!整個拍攝過程,就是在這樣無力卻又亟於從繁複、停滯的重建狀態中脫困的心情裡反覆煎熬。
然而,當所有有形無形的災難趨於絕望頂點之時,人,總會在絕地處找到再生的機會,記錄直到第二年,我所記錄的在地青年廖學堂與他們村內三十幾位鄉親發起的『福盛圳』復圳行動,成了絕地逢生中一股人心的救贖,它讓中寮人在困頓膠著的重建狀態下,讓我在無止盡的拍攝無力中,看到一絲光明的希望,如同嚴冬將盡,暖春來臨前,乾凅的土地中抽露的一抹新芽。
這六年來,『在中寮相遇』這部片子,跟我的親密貼近,無人可取代,所夢,所思,所念,都是它,午夜夢迴、行車等候之際、慢跑休憩的片刻,它像一個隱形的親密伴侶,隨時在我身側,如今,它將離開我,成為一部獨立的片子,突然,我有一種悵然若有所失的感覺!
而今,我已將這部片子妝扮完成,足足剪出了三集,五個多小時的長片,或許,在現今快速的生活步調中,要把這部長片一口氣看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誠摯地邀請大家有空來看看這部片子,認識我在中寮相遇的那群可愛可敬的朋友。
最後送給大家一首詩,這是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於1755年11月,里斯本強震之後所寫的一首詩---
這幾年,每當我面對拍攝現場感到無力可施之際,或是因為苦思剪接而輾轉難安之時,我便會回頭細讀我抄寫在剪接札記扉頁的這首詩,它總能安定我躁動的心神,讓我重新回到創作的原點。
對了,我是這世界裡一個弱小的角色,
但是,一切的生物,一切有感覺的東西
都和我一樣的受罪,也一樣地不免於死,
兀鷹攫住一只懦弱的小鳥
牠那血淋淋的嘴喙住那顫抖的肢翼,
這樣,對於兀鷹來說,一切確是非常圓滿,
可是,頃刻之間,一隻鷹鷲卻把這兀鷹撕得粉碎
這時,地上有個人,一箭射穿鷹鷲;
但不久,他自己卻也倒在戰場,
血染四週已經戰死的夥伴,
又變成了餓鷹的糧食,
世事便是這樣週而復始,
到處充滿苦痛的呻吟。
可是,在這群魔亂舞的世界裡
你還要說,個別的不幸構成全體的幸福!
多幸福!於是你,這可憐的人,
用顫抖的聲音喊著:「一切都很圓滿」,
可是,世界證實了你的話不過是謊言,
你的內心也千百次地駁斥你自己的幻想….
最曠達的人對此有何高見?
安靜罷!因為宿命原不可知!
人類也看不到本身的廬山真面,
他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往何而去?
一生勞碌,就像泥土上滾動的灰塵一樣
受著命運的玩弄,等待死神的吞噬;
可是,有思想的微粒,卻能用他們遠視的眼睛
於是,我們和無限的宇宙竟然成了一體,
但是,卻永遠不能把自己弄得水落石出。
這世界,這衿誇而荒謬的劇台上
擁擠著許多令人作嘔的愚人,
他們都在談論著快樂
從前,我也曾一度用不太悲哀的語調
歌頌著世俗上快樂的人生之道,
但時代已經不同了,經過這麼多年的教訓
再加上體驗到人類的許多弱點,
至今,我只能忍受一切,不再怨尤
希望在這愈加黑暗的時候,尋求一線的光明。
本篇圖文著作權為黃淑梅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影展與獎項
2006 台北電影節
2006 台北電影節
2006 南方影展 - 南方獎(首獎)
2006 南瀛獎 - 紀錄片首獎
2006 台北電影節 - 評審團特別獎、媒體推薦獎

